连日阴雨不停,交通被阻,他被迫待在深山里,心里那个急呀。后来打听到一条山间小路,可以去到他急着要赶去的林场场部。于是他顶着零星小雨上路了。
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突然一不小心跌下了一条沟壑,他慌乱得什么都没来不及抓住,只好闭上眼睛,任由自己往下跌去。还好的是,最后他抱住了一棵柏树。他吓呆了,四处望望,有一条河,还有一座木桥。非常好运!之前跌落沟壑,并没有要了他的性命,反而将他送上了一条通往林场场部之路。

(潘小娴摄)
于是,他走向那座木桥,陶渊明之诗,却像那木桥下的河水,在密林里,在整个天地间流淌不止:“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
看完这个故事,我真是为书中的这个“他”的心态折服,雨夜赶路,遇事不慌,既来之则安之,最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来上了这么诗情画意的陶渊明“今日天气佳”。那真是,心中有诗,一切皆好。

(潘小娴摄)
这个“他”出现在《诗来见我》(李修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其中“陶渊明六则”中的人物。为了谋生,“他”无时不再窘境中挣扎,这期间,深壑中的一棵柏树,盲人的一段评书,或是散落窗前的莜面窝窝皆为“他”的救命稻草,此外更为重要的当属陶渊明,那些诗句不仅是“他”的宿命,更是良药——穿越山水与生死间,“隐逸帝”随时伴我身边。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首属于自己的诗!“他”喜欢上了陶渊明的诗句,不论人生如何碰上什么境遇,“他”的双脚所及之处,陶渊明之诗就好像是一路上的车站,总能在千山万水里与他相见,给予他人生光明与慰藉。诗与远方,一直就在他的眼前,他的心中。

《诗来见我》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李修文的散文集,通过古典诗词叙写人生际遇,通过古今对话见证自我完成。作家将一首首古诗与当下的个体生命与人生际遇相连接,感知每个人身上那份挣扎于生活时产生的勇气与赤诚。
古人的诗,其实不只在书里,而是会在我们的命里,会在我们的路上。作者李修文说,“我们中国人,无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中,总有那么一句两句诗词在等待着我们,见证着我们,或早或晚,我们都要和它们破镜重圆,互相指认着彼此。”
连日阴雨不停,交通被阻,他被迫待在深山里,心里那个急呀。后来打听到一条山间小路,可以去到他急着要赶去的林场场部。于是他顶着零星小雨上路了。
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突然一不小心跌下了一条沟壑,他慌乱得什么都没来不及抓住,只好闭上眼睛,任由自己往下跌去。还好的是,最后他抱住了一棵柏树。他吓呆了,四处望望,有一条河,还有一座木桥。非常好运!之前跌落沟壑,并没有要了他的性命,反而将他送上了一条通往林场场部之路。

(潘小娴摄)
于是,他走向那座木桥,陶渊明之诗,却像那木桥下的河水,在密林里,在整个天地间流淌不止:“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
看完这个故事,我真是为书中的这个“他”的心态折服,雨夜赶路,遇事不慌,既来之则安之,最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来上了这么诗情画意的陶渊明“今日天气佳”。那真是,心中有诗,一切皆好。

(潘小娴摄)
这个“他”出现在《诗来见我》(李修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其中“陶渊明六则”中的人物。为了谋生,“他”无时不再窘境中挣扎,这期间,深壑中的一棵柏树,盲人的一段评书,或是散落窗前的莜面窝窝皆为“他”的救命稻草,此外更为重要的当属陶渊明,那些诗句不仅是“他”的宿命,更是良药——穿越山水与生死间,“隐逸帝”随时伴我身边。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首属于自己的诗!“他”喜欢上了陶渊明的诗句,不论人生如何碰上什么境遇,“他”的双脚所及之处,陶渊明之诗就好像是一路上的车站,总能在千山万水里与他相见,给予他人生光明与慰藉。诗与远方,一直就在他的眼前,他的心中。

《诗来见我》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李修文的散文集,通过古典诗词叙写人生际遇,通过古今对话见证自我完成。作家将一首首古诗与当下的个体生命与人生际遇相连接,感知每个人身上那份挣扎于生活时产生的勇气与赤诚。
古人的诗,其实不只在书里,而是会在我们的命里,会在我们的路上。作者李修文说,“我们中国人,无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中,总有那么一句两句诗词在等待着我们,见证着我们,或早或晚,我们都要和它们破镜重圆,互相指认着彼此。”


“汪泉的小说致力于开掘人性的幽微,洞察人心的隐痛,触摸人类共通的善意,彰显人类隐蔽的美好,突破了一般小说的叙事窠臼,文本内里投射出神性的光芒,创造了别样的文本景观,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莫大的收获和至高的追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年近八旬的作家刘斯奋先生亲笔撰文推荐作家汪泉创作的中篇小说集《阿拉善的雪》。

《阿拉善的雪》(汪泉/著,太白文艺出版社),由四部中篇小说构成,均在《小说月报》(原创版)、《飞天》等发表过,分别为《相拥》、《家雀》、《黑面条》、《阿拉善的雪》构成,属于作家精选的小说力作。四部中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家雀,有序描写了主人公家雀的童年、少年、青年三个阶段的成长史,完整构成了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以旷远、阔大、凌厉的河西走廊以及内蒙古阿拉善等为地域背景,以家雀在河西走廊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经历为主要内容情节,描摹了二十世纪末中国西北大地上独具特殊意义的时代和人性变迁,描写了家雀从偏远的祁连山褶皱里竭力试飞,进而像麻雀一样,努力拨开大山般的遮蔽,让肉体和精神得以飞翔。

小说家只讲“好看”的故事还远远不够!汪泉认为,对弱者的同情是一个小说家的使命之一,但刻画背负着隐痛而与命运抗争的人,对其隐痛或对看似强者的隐痛的描写更应是文学的一大使命。此外,该书配有香港插图师陶炜创作的精美插图,为小说文本增添不少亮色。

《从农业1.0到农业4.0》(温铁军/著,东方出版社),是温铁军教授团队历时3年的研究成果,是继《八次危机》《去依附》《全球化与国家竞争》之后的又一部重磅作品。作者认为,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农业一直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然而自17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所主导的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城市崛起,乡村凋敝,工业文明飞速发展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和农业困局,农业困境和人类文明的出路在哪里?答案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产业化农业向农业可持续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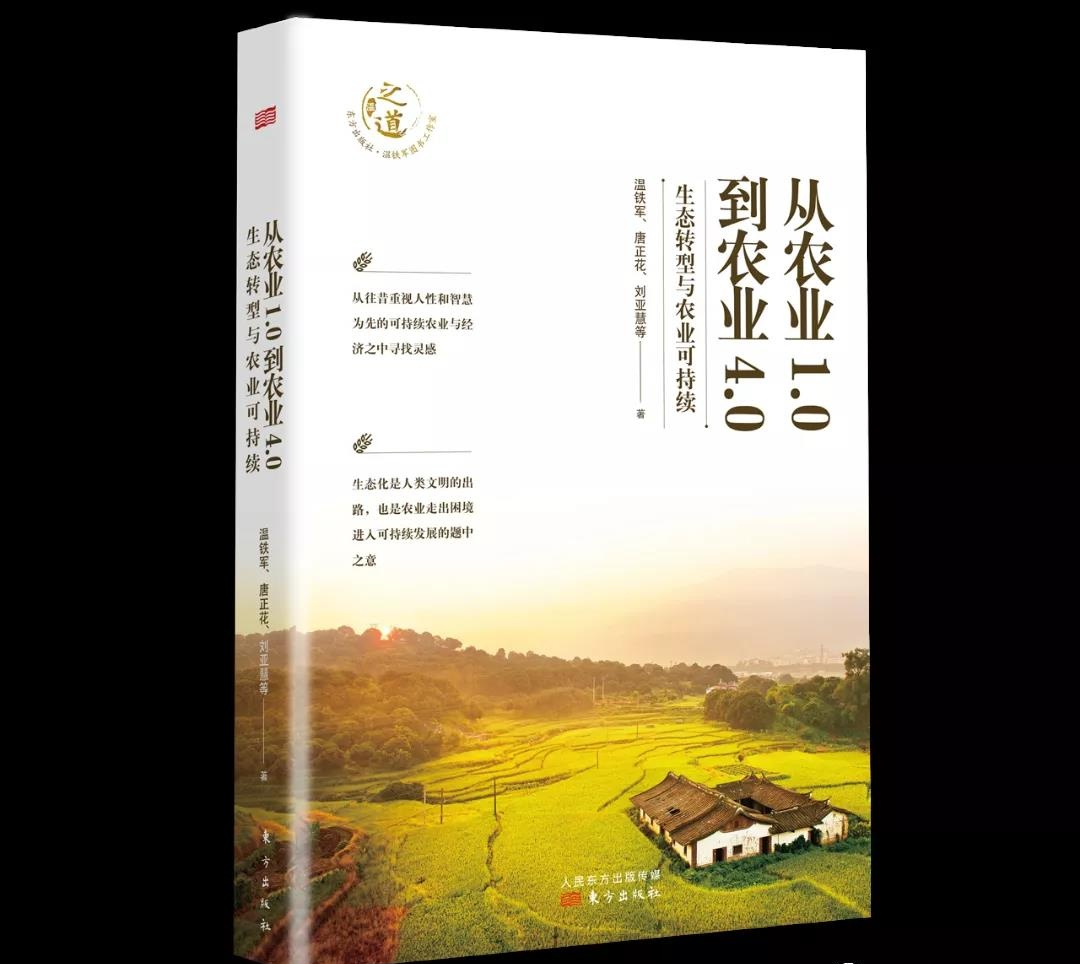
全书以人类文明发展受气候变迁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竺可桢假说破题,以最新的“浙江人”考古发现为重要依据,从宏大的历史和地理视角论述了气候变迁、各大洲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于农业多样性起源的深远影响。全书不仅对于农业发展的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对于近代以来世界农业发展模式三分天下的格局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更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介绍了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丰富经验。

